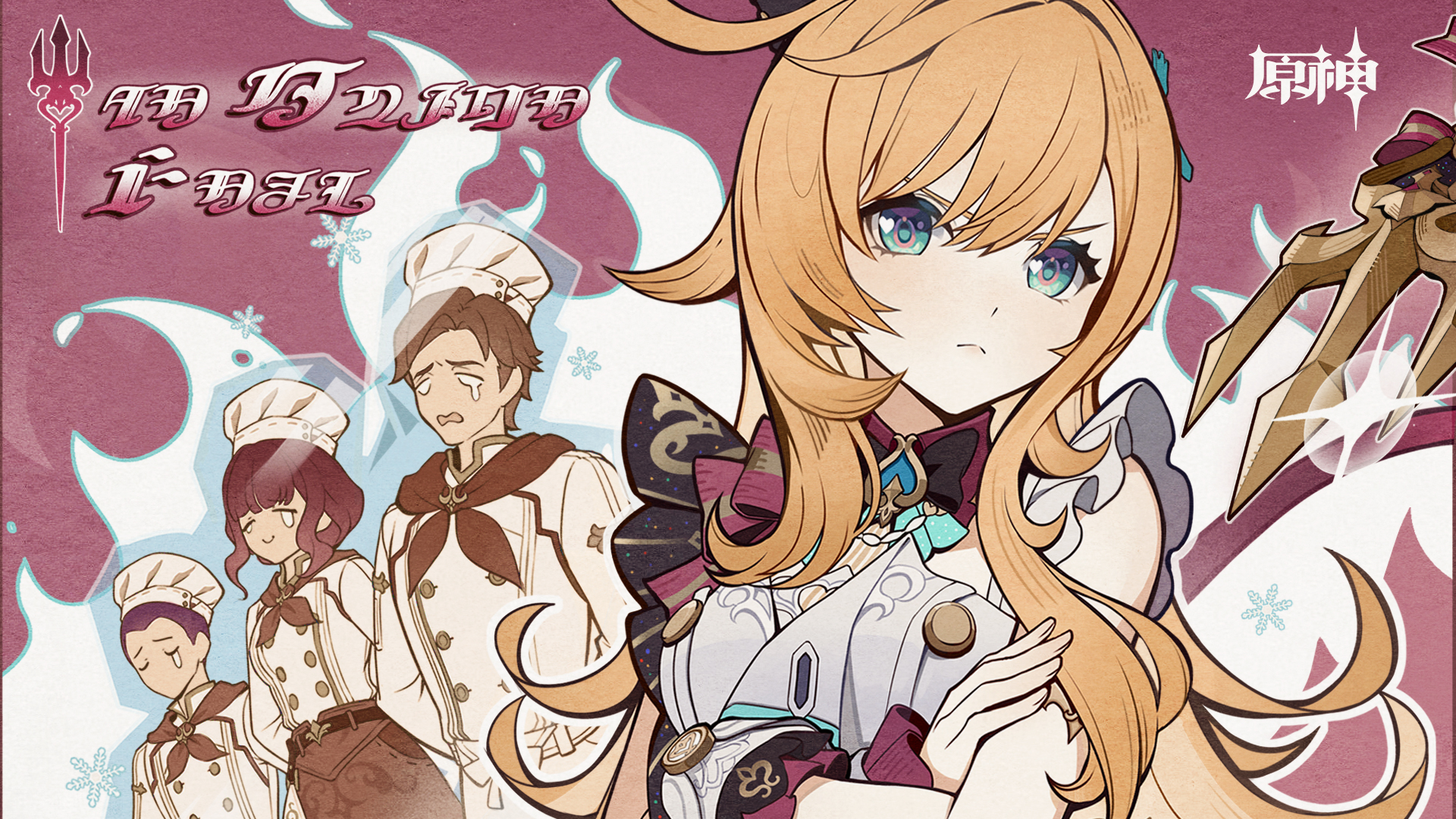听《二泉》
无锡某处的阿炳雕像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。乍看上去,他好像并非哪里的伟人,竟是和芸芸众生一样,受难之后低下自己的头颅,满不在乎地继续生活。但他谦卑地戴上帽子,架着圆形的墨镜,支起二胡,撑开右臂,彷佛将要用磅礴无尽的力量推出弓时——时间于此刻凝固。
一些演奏会上的二泉映月,技巧高超,细节饱满丰富,还有很多其他乐器的伴奏,但是却不一定能像这个视频里的一样触动人心。
事实上,如果能“有幸”见到一个真正的靠着街头卖艺讨生活的人,你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:人是被命运卷入其中的。
十几年前,C 市的路上还跑着数不清的人力三轮,市中心(现在已是旧城区)的街道边,或是唯一一家肯德基的门店前,常常能遇到这样的卖艺人。他们的技巧非常粗糙,甚至可以说是刚刚能把音发出来,有人的琴不知是不是自己做的,弦还打着结,一个非常简陋的,送别人都没人要的琴。然而就是这样的琴,拉出的二泉(也许还是和同行学的),却最能撬动人心设防的深处。因为那些演奏会上的二泉,太过从容,太过华丽,太过完美,也太过奢侈了。而这些街头的人,才构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真实图景的一角。
这种感情是人类共通的,德富芦花曾写道:
呜呼,我本东西南北人。我曾经夜泊于赤马关外,和着潮声而慷慨悲歌;我曾经客旅于北越,夜闻离别之曲而悲泣。我曾经于月明风清之夜,耳听着中国海上的欸乃之声;又曾经在一个雪天的清晨,行进于南萨的道上,听赶马人的歌唱。这些都打动了我的心扉。而那街头的一片市声,却不能使我肝肠寸断。
中国宣布全面脱贫的夏天,我在上海见过皮肤黝黑、赤裸着上身流浪乞讨的男人。蜗居北京的日子里,也遇到不少在北京西站负一层躺下休息的男女、孩子,也许我的境遇也只比他们好一点。
德富芦花在听 Still sad music of humanity 时,感受到无数不可名状的苦恼,无数的鲜血,无数的眼泪。
这固然是深刻的体会。而我在《二泉》中感受到的情愫,与下面两句诗颇有相通之处:
春风桃李花开日,秋雨梧桐叶落时。
西宫南苑多秋草,落叶满阶红不扫。